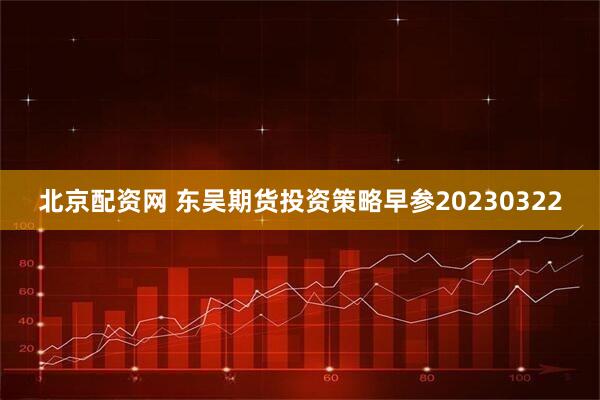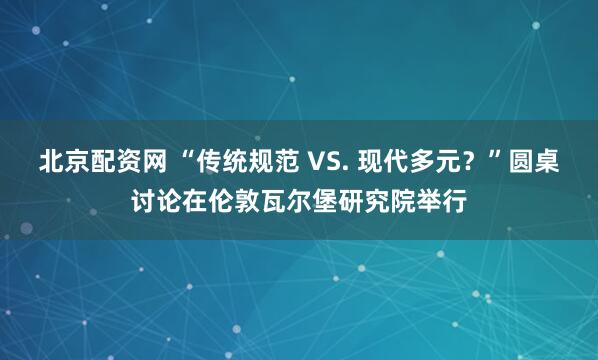
 北京配资网
北京配资网


圆桌讨论现场

利奥妮·贡布里希作为贡布里希家族的代表,受邀主持本场圆桌讨论
近日,由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与瓦尔堡研究院主办的“传统规范 VS. 现代多元?”圆桌讨论,在伦敦瓦尔堡研究院举行。
贡布里希的遗稿保管人利奥妮·贡布里希[Leonie Gombrich]作为贡布里希家族的代表,受邀主持本场圆桌讨论,共同庆祝文集《贡布里希之后的全球文化:艺术、心灵、世界》[Global Culture after Gombrich: Art Mind World]的出版。这本文集由2019年10月25日至27日于中国美术学院举办的“心灵·艺术·价值:纪念贡布里希110周年诞辰国际会议”上十位国际知名学者的演讲整理而成。就“传统规范 VS. 现代多元?”这一议题,她请大家尤其注意标题中出现的问号,相较于传统规范与现代多元的对立,她更期待听到在场嘉宾对两者关系的具体看法。
利奥妮随后介绍了台上五位圆桌讨论的与谈人,他们分别是瓦尔堡研究院院长比尔·舍曼[Bill Sherman],中国美术学院资深教授、贡布里希和哈斯克尔的学生曹意强,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英国东安吉利亚大学世界艺术研究学院荣休教授、英国艺术史家协会学刊《艺术史》创刊主编约翰·奥奈恩斯[John Onians],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英国国家美术馆前任馆长尼古拉斯·彭尼爵士[SirNicholas Penny],以及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艺术人文学院院长、瓦尔堡研究院访问学者范白丁。从上述简介已能看出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与瓦尔堡研究院密切的联系。
在正式将时间交给与谈人之前,利奥妮讲述了她对瓦尔堡研究院的初印象。1976年6月,当时9岁的她来到瓦尔堡研究院参加祖父贡布里希的退休派对,年幼的她早已不记得当年讲话的具体内容,但仍清晰记得贡布里希表达了自己对这所从汉堡迁移至伦敦的研究院最诚挚的感谢,并希望瓦尔堡研究院能继续延续阿比·瓦尔堡[Aby Warburg]“智性的勇气”[intellectual courage],大胆提问、找寻答案。贡布里希退休后并未完全离开研究院,他仍在这里举办讲座、会见师生,利奥妮也常在研究院楼下传说中的“瓦尔堡咖啡馆”与他碰面,那里的氛围让利奥妮怀念不已。由于这几年的改造计划,咖啡馆今已不再,变成了档案室,但利奥妮重提咖啡馆是因为她对那儿最清晰的回忆,来自其祖父于1989年3月在那儿举办的80岁生日会,还有她祖母的钢琴,经过修复后,也被放置在今天的会场,以及祖父来到瓦尔堡研究院工作后设立的接待处,多年来在此工作的员工、学者,所有都构成了她对瓦尔堡研究院的美好回忆。最重要的还有这所机构所代表的提出问题的“智性的勇气”,相信也是本次活动大家要探讨的重点之一。

圆桌讨论现场
曹意强
Cao Yiqiang
曹意强老师首先发言(全文见文末链接)。他重点谈到了中国美术学院与瓦尔堡研究院之间深厚的学术渊源,并指出新发布的书籍《贡布里希之后的全球文化:艺术、心灵、世界》是这种合作的成果之一。他提到,从2019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心灵·艺术·价值:纪念贡布里希110周年诞辰国际会议”到本书出版的五年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使得本书显得愈加相关。他认为,在如此不确定的时代,贡布里希所捍卫的人类文明一体性(the unity of civilization)和对去人文化倾向(the dehumanization of the humanities)的忧虑,对我们应对当前挑战具有重要的警示和启发意义。最后,曹意强老师希望这本文集能为思考当下全球挑战提供一些启示。

曹意强发言
约翰·奥奈恩斯
John Onians
约翰·奥奈恩斯则分享了他在阅读贡布里希《秩序感》[The Sense of Order]时的一些感想,亦即贡布里希提到的“生物遗传性”[biological inheritance]。当人们尽量都在避免探讨文化现象植根于生物遗传性时,奥奈恩斯认为贡布里希提出这个概念是非常有勇气的。奥奈恩斯承认自己和其他任何人一样,都在试图理解人类心智的活动究竟为何,他之所以提到“生物遗传性”,也恰是因为这一话题今已不再时髦。如今的人们不愿去直面生物遗传性的真正含义。这让奥奈恩斯更有动力去了解它的含义与意义,于是他研究大脑的构造,探究其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但他想超越陈词滥调、哲学空谈和语言层面的指摘,由此而来的成果也是这些年来他为艺术史领域所作的贡献。
对奥奈恩斯而言,这些年的研究使他意识到正是生物遗传性将普遍性的事物汇聚在一起,每个人都具有这套生物“设备”,但每个人对它的运用却截然不同。在奥奈恩斯耳中,他在听任何人说话时,听到的实则是他们过往经历的共鸣。比如他在听贡布里希讲话时,就能在感受他话语中所带的浓烈维也纳口音中想到他过往的经历。事实上,如果贡布里希的声音缺失了这种口音,他的话语也就不会有同样的力量。
奥奈恩斯最后指出,他很高兴大家齐聚一堂,再次基于个人经验进行分享,他想请所有人记住,这些个人经验就生理层面而言,都是建立在神经化学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些可能性,组成了这个仍然美妙的世界。
尼古拉斯·彭尼
Nicholas Penny

尼古拉斯·彭尼发言
尼古拉斯·彭尼随后发言。他首先感谢了于2019年的纪念贡布里希诞辰110周年会议,以及文集《贡布里希之后的全球文化:艺术、心灵、世界》的出版,这才让大家此次重聚于瓦尔堡研究院。彭尼借此机会,又去重读了贡布里希的一些著作,他选取的是他不太熟悉的出版于1979年的《理想与偶像》[Ideals and Idols],书中包含了贡布里希于1961年12月8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发表的演讲,其中还包含了一段贡布里希与中国格外相关的内容。
贡布里希在这篇名为“普通知识的传统”[The Tradition of General Knowledge]的演讲中,谈到了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益处。彭尼承认这让他想起了自己年幼时在学校刚开始学拉丁语的景象,当时也有过这些争论。彭尼说那时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要学习一门死去的语言,亦不认为这两门语言能从某种程度上训练思维。因此,他十分乐于见到贡布里希说“我不明白为什么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要比同样深入地学习中文对于培养智力更有效”。贡氏还说:“是我们的文明为人们提供了学习经典作品的可能性,其理由很简单:我们的祖先培养了这些古典作品。”彭尼认为贡布里希的这些表述既是意料之外,又极具深意。
彭尼接着提到了这本书中的另一篇稿子,是他在杭州的贡布里希图书馆所见:“视觉艺术的准则与价值:与昆汀·贝尔的通信”[Canons and Values in the Visual Arts: A Correspondence with Quentin Bell],写于1975年。彭尼提到了贡布里希在书信中举过的一个例子,他让一位学生去V&A博物馆观赏拉斐尔的大样[Raphael cartoons],不过学生回来说她其实不太喜欢这些画稿。贡布里希在信中继续写道:“我冷冷地告诉她我并不关心你的喜好。”彭尼指出这话虽有点残酷,但在上下文中,贡氏表达了一个他早前提出的观点:即这些作品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学生必须了解、思考它们。贡氏确实在以他自己的方式捍卫着某种传统。
彭尼最后还指出,在1961年的那篇演讲结尾,贡布里希曾提出了一份西方文明信经的初稿方案,在彭尼看来,读起来不似《世界小史》[A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而更像一本《小世界小史》[A Little Little History of the World]堪称一份极其扼要、浓缩的世界史,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份关于他在其中立场的宣言:“我属于西方文明,于公元前一千年诞生于希腊……”贡氏的阐释非常谨慎,仔细地在其对欧洲文明构成的描述中包含了其他文明。最后,贡氏说:“在我们这个世纪,西方文明还危及和改观了地球上其他民族的文化……不过,我希望我们的文明还会有二十一世纪。”彭尼认为理解贡布里希极其重要的一点是,他确实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扰,但同时他对那场冲突某些方面所隐含的意义也有着更深刻的理解。正是这激发了他关于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Hegel]的写作,其力量必定让英国许多人感到费解。因为实际上,即使是英国最具学识的人,也没有多少人曾真正严肃对待过黑格尔。哪怕有例外,彭尼仍认为贡布里希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高估了黑格尔主义作为一种大规模“思想瘟疫”[intellectual disease]的程度。
但彭尼还是认为贡布里希可能是对的。毕竟他想不出有什么比贡布里希的文章“寻求文化史”[In Search of Cultural History]更精彩的论述了。贡布里希在这篇文章中追溯了黑格尔主义的起源,并揭示它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的著作。这尤其重要,不仅因为贡氏十分敬重布克哈特,同时这也是贡氏所承认的一种无意识的智性影响[intellectual influence]。彭尼认为,在欧洲思想史的论述中,这种洞见从未被超越。
彭尼认为贡布里希的著作中有许多观念,在今天看来显然已不适用,因其源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智性世界——而这正是贡布里希会欣赏的一种褒奖。因为你要学会区分那些明辨事物差异的人,和那些捍卫特定传统及思维方式的人。贡布里希与其说是一个传统主义者,不如说是一个始终倡导我们应努力建立联系的人。那正是他所谓的思维习惯[habit of mind],即寻求连续性的习惯。这也是为何我们要去学习古典作品——当然,如果我们也能致力于学习中文,那就更好了。
范白丁
Fan Baiding

范白丁发言
范白丁老师紧随其后发言。他深感荣幸能代表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出席此次活动,提到当自己仍在学习艺术史时,贡布里希的著作就是必读书目。而杭州的贡布里希纪念图书馆时刻提醒着他艺术人文学院和瓦尔堡研究院之间跨越数十年的友谊,以及一位伟大学者不朽的人文精神。
范白丁也提到贡布里希曾在演讲中,把学者的图书馆比做艺术家的采石场,图书馆意味着记忆和传统,而人们的知识和艺术正来源于此。瓦萨里深信,艺术家相互学习,并能在前人的成就与发现之上添砖加瓦。范白丁认为学术研究亦复如是,一如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会被要求阅读贡布里希的著作。全球范围内,或许在某些艺术史课堂上,贡布里希已被贴上过时的标签,并被更多元的视角与方法所取代。当然,大家都乐于见到艺术史这门学科的不断反思和持续生长。但在贡布里希或者潘诺夫斯基这样在今天或许被认为旧式的学者身上,他仍然看到并深深欣赏一种人文主义式的治学态度,借用潘诺夫斯基的话来说:“人文主义者拒斥权威,但他尊重传统。”他相信这种态度有助于大家更好地面对本次会议要探讨的两个主题。同时,范老师还提到人文学科的另一种特质,就是其对人类心灵的深切关怀,这种关怀他曾在2019年杭州会议的现场有过切身体会,而这次他很高兴看到同样的精神得以在这本文集中呈现。
范白丁还向文集出版社[Intellect Books]和瓦尔堡研究院致以诚挚的谢意。

比尔·舍曼
Bill Sherman
瓦尔堡研究院院长比尔·舍曼作最后的总结。他首先感谢了利奥妮担任活动主持人,接着重提了利奥妮开场时提到的那场1976年贡布里希退休时的演讲,那是一篇和尼古拉斯·彭尼提到的1961年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讲稿一样的真正的演说辞,对于舍曼而言,他也经常引用其中的话语,即对于瓦尔堡研究院的感激之情,以及保有提出问题的勇气。但他提出利奥妮遗漏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那篇演说采用了古典风格的正式措辞,向命运女神福尔图娜[Goddess of Fortuna]致敬,这关乎他所感受到的幸运,他从命运女神那里得到的善待——这也是瓦尔堡本人所痴迷的主题之一。众所周知,记忆女神谟涅摩绪涅[Mnemosyne]之名刻于瓦尔堡研究院门楣之上,因此可以说记忆女神是这个机构最主要的联系。但舍曼认为,瓦尔堡研究院同样要向命运女神福尔图娜致敬。贡布里希在那篇感人至深的演讲结尾部分,还提到了那些激励他持续提出艰深问题的人们,以及同袍情谊和对知识的热忱——正是这些真正定义了他自1936年至2001年于瓦尔堡研究院的经历,这确实是一段极其漫长的学术共同体时期。
舍曼由此引申,提到自己能在瓦尔堡度过8年时光的幸运。这8年见证了诸多艰难之事。正如曹意强老师所言,回想5年前——即距2019年纪念贡布里希诞辰110周年会议仅几个月后,疫情随即爆发,范白丁还被困在武汉家中,真是恍如隔世。2020年,英国经历了脱欧,再到如今,欧洲和中东皆陷于战火。因此,这是一个艰难的时期。然而,瓦尔堡研究院再次给予我们慰藉,让我们知道自己终究是幸运的,是受眷顾的。舍曼仍记得研究院曾关闭数月之久,当时他们在演讲厅举行了最后一次聚会,互相打气说瓦尔堡研究院已经历过最坏的时刻,大家都会安然无恙。舍曼希望现场来宾原谅此刻流露的些许感伤,因为这次活动确实是一次重逢,让他得以见到许久未见的很多人。他也向来到现场的(也参加了2019年会议)惠特尼·戴维斯[Whitney Davis]与帕塔·米特[Partha Mitter]致敬,并请大家务必购买文集并仔细阅读,里面不仅有彼得·伯克[Peter Burke]关于文化观念的精彩论述,也有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等多人的文章,文集所汇聚的,恰是那些真正将贡布里希的遗产,以优美文字带入艺术、心灵、价值与世界等议题加以探讨之人。
最后,比尔·舍曼再次感谢了到场的所有人,重申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命运女神福尔图娜的精神指引。

文集撰稿人惠特尼·戴维斯与帕塔·米特参与讨论

圆桌讨论观众席
来 源|艺术人文学院
编 辑|黄筱柔
责 编|邱莉丽
审 核|徐 元 范白丁
中国美术学院官方微信号
投稿邮箱:caanews@caa.edu.cn
“国美学术通讯”官方微信号
投稿邮箱:caarmt@caa.edu.cn
出品:
中国美术学院党委宣传部
PUBLICITY OFFICE OF THE CPC CAA COMMITTEE
CAA融媒体中心
CAA MEDIA CONVERGENCE CENTER

铁牛配资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